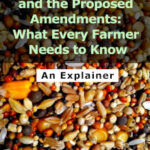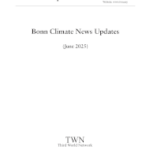四川凉山州彝族传统医药知识调查
作者:赵富伟
研究人员于2007年4月在四川凉山地区开展了有关彝族传统医药知识的调查,采访彝族传统医生及彝族医药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了解彝族医药在民间的存在现状和有关传统医药知识获取及惠益分享的问题,并对部分彝族传统医生的医药学知识及病案做了声像记录。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南至金沙江,北抵大渡河,东临四川盆地,西连横断山脉。处在东经100°15′~103°53′和北纬26°03′~29°27′之间。气候宜人,素有“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之称,被誉为“天然的塑料大棚”。凉山历史悠久,秦汉即置郡县委派官吏治理。新中国建立初期,凉山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奴隶社会,土司政权强大,家支林立,等级森严。1956年民主改革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凉山建立,标志着凉山彝族人民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性跨越。
彝族是先秦时期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氐羌族群的一部分南迁后,融合当地土著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秦汉之际彝族先民就已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凉山州是彝族群众的传统聚居区,除彝族外还居住着回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据2003年人口统计数据,全州彝族180多万人[1]。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曾被称为“夷经”、“爨文”、“罗罗文”等,通称老彝文,1980年新彝文推广使用。
彝族传统信仰“毕摩教”(一种以祖先崇拜为核心,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为一体的传统信仰),拥有特殊技能和文化素质的“毕摩”和“苏尼”是祭祀、巫术、兆卜、禁忌等信仰活动的中心人物[2]。彝族传统社会巫医不分,承担宗教职能的毕摩和苏尼同时也承担为患者消除疾病痛苦的医者职能。由于毕摩和苏尼治疗疾病多采取宗教仪式而非医学手段,并且毕摩和苏尼的宗教功能已有多方关注,故在本次调查中较少关注,侧重于采用医学手段诊治疾病的传统医生。传统医生在诊断疾病时常使用“取象诊断法”(具体分为三种即剖鸡取象、滚蛋取象和剖羊取象)和“方位推算诊断”(俗称“算病”),彝医药学者阿子阿越所著《彝族医药》中有详细介绍。此类诊断方法明显具有巫医结合的特点,长期存在于彝族社区,为广大彝族群众所接受。
彝族有独立于中西医的医药学体系。彝族史书《勒俄特依》中记载:“吹风成了气,吹风成了力,吹风成了毒,成了千万毒,所有病邪从此来”;“风成了箭,雨成了箭,木柴成了箭,大鸟成了箭,野兽成了箭,树木石头成了箭”;此外还有诸如狗毒、兽毒、蛇毒、蛙毒等各种毒症的记载。根据调查中发现的彝族古书《勒俄阿布》等(彝族传统医生木吉约恰家传珍藏)记载,疾病大致分为风证、箭证、蛊证、传染病等20余种,各病症之下再细分为若干种病。彝族传统医生的诊法分为望诊、问诊、闻诊、嗅诊、切诊、取象诊断法、方位推算诊断等。治疗方法不一而足,主要有敷治法、擦治法、烧治法、熏蒸法、洗浴法、刮治法、提筋法、针刺放血法、取治法等等。彝族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彝医药书籍中记载的药物大致在700种左右[3]。据木吉约恰介绍,他认识800余种药物,曾经和西昌某彝族医药研究机构合作收集、整理这些药物的标本。
彝族民间存在着许多具有独特疗效的诊治妇科病、肾炎、胃痛、心脏病、狂犬病、风湿、痛风等疾病的传统医药知识。治疗胃病使用八月瓜和猪肚,具体做法是:取八月瓜果实、根、茎、叶若干,切片,塞入新鲜猪肚中,煮食猪肚并饮汤,服食两三次即可痊愈。狂犬病诊治方法别具一格:其法一,诊断时可让患者(不论是否发作)吃一种生的豆类,如果觉得味道香甜,越吃越想吃,就证明体内已中疯狗病毒,如果食不下咽则体内无疯狗病毒;其法二,让病人端坐,以酒喷其背心,汗毛交织在一起则证明体内已中疯狗病毒。治疗方法有:其一,用红豆煮食,天天吃;其二,用仙人掌熬水吃或炖瘦肉吃;其三,以虎骨刮末吞酒。木吉约恰先后于1945年、1949年、1952年治愈患狂犬病的病人,疗效甚佳。
彝族传统医药是彝族人民智慧创造的历史成果,是彝族群众对病因、病理、诊疗方法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存在着两种传承方式,即口传心授和文献传承。历史上,彝文只被少数人掌握,民族文化的传承部分依赖口传心授。彝族医药通常是师徒相传或父子/母女相传。徒弟或子女跟随师父或父母上山采药和出诊,在此过程中师父或父母口授与药物和诊疗有关的知识,指导徒弟或子女为病人施诊,徒弟或子女用心记忆并在实践中总结自己行医用药的经验。徒弟或子女到一定年龄后学成出师,传统医药知识的代际传承得以完成。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这使彝族先民的智力创造得以保存并传承至今。迄今整理出版的彝族医药文献得益于在民间发现的彝文古籍,许多彝族传统医药知识在毕摩经书或彝族史书中均有记载。但是,随着汉字和汉文化的传播,传承彝族传统医药知识的这一载体正在受到威胁。历史上,毕摩是彝族群众中唯一能运用彝文的群体,因他们的传承体制严密从未间断使得用老彝文写成的经书及其他书籍能流传下来。新彝文虽是在老彝文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与老彝文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教育体制下的青年学习的是1980年以后推广使用的新彝文,青年人不能运用老彝文记载的古籍,其中的许多传统医药知识面临失传的危险。另外,由于传统上医生为病人诊治疾病不推崇收取费用,行医并不能作为医生的生计方式,青年人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般不愿学习传统医学,许多传统医生收不到继承衣钵的传人。虽然学界有许多彝族医药的文献已经整理出版,但由于研究者多侧重理论的总结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临床研究,使彝族医药难免成为书本上的传统知识。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传承的形势严峻。
忽视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传统知识的持有人还是科研机构都没有充分重视持有人有关传统医药知识的权利。持有人的普遍心态是“谁有用谁拿去”,通常会将自己的药方(祖传秘传除外)告诉和自己“交情深厚”的人,而这些人不乏为制药企业服务的工作人员。科研机构则认为提供医药信息的当地人并不注重提供信息后获得的回报;另外,新药开发不可能完全按照持有人提供的原方开发,都要经过研究者去粗取精重新组方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成果和原方常有着根本的差别。因而,当研究人员从持有人那里获得药方后,持有人不会向研究者索取回报,研究人员至多出于道义给予持有人一定的报酬(通常是赠送小礼品或少量现金)。他们从未思考过将此种回报制度化的问题,因此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公平的惠益分享。
彝族医药遭受生物海盗的潜在危险超过笔者的想象,研究机构、制药企业对彝族医药知识的收集和开发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加强的趋势。阿子阿越透露,其利用母亲传授的治疗痛风的彝药方开发出的“痛风灵”已经受到国内甚至国际上多家企业的关注,这些企业曾通过多种途径向阿子阿越询问配方。出于一个研究者的警惕性,阿子阿越并没有轻易将药方拱手送人,直到最近才和江苏某制药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决意开发彝药“痛风灵”。并非每个研究彝族医药的人都有阿子阿越这般的谨慎,难免抵挡不住某些开发商的巧取豪夺,彝族传统医药知识流失的危险令人担忧。
[[1]] http://www.lsz.gov.cn/html/lsztemplate_1.asp?catalogid=93,2007年5月13日浏览。
[2] 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出版社,2003.5:p224 。
[3] 阿子阿越编著,《彝族医药》,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4:p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