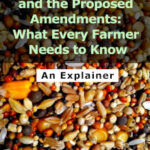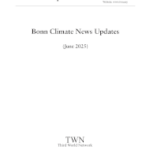哈尼族习惯法对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探析
作者:杨京彪
一、前言
哈尼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社区内部形成了村规民约,或者称之为习惯法。由于哈尼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其习惯法以口头规定形式存在于哈尼人的观念中,并引导着哈尼人的行为。哈尼族习惯法虽然不是成文法规,但具有事实上的法律效力,其裁决者与执行者是村寨头人、有威望的长者、村民大会等,其惩罚的执行方式并非采取强制性的暴力方式,而是依靠信念,即对宗族、村寨的归属感,在哈尼族习惯法中最严重的惩罚莫过于逐出家族和村寨。哈尼族习惯法涉及范围极广,几乎覆盖了哈尼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些规定灌输在哈尼人的思想观念当中、贯彻在哈尼人的行为实践当中,为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哈尼族习惯法逐渐在变化。其最大的变化是由口头规定转变为文本形式,现在,许多哈尼村寨都制定了文本形式的村规民约。
二、调查概况
笔者于2009年7月份赴云南省元阳县进行田野调查,调查主要采用了关键人物访谈法,对村委会成员、摩批、咪谷以及村中有威望的老人进行访谈。期间共走访了箐口村、大鱼塘村、全福庄、麻栗寨、坝达村等哈尼族村寨,搜集到三份文本化的村规民约,并挖掘出一个案例。
三、调查结果
现以云南省云阳县新街镇箐口村、大鱼塘村、全福庄、红河县乐育乡尼美村委会坝美村、窝伙垤村委会倮厄村、绿春县大兴镇岔弄办事处倮别新寨等六个哈尼族村寨文本形式的村规民约为例[[1]],研究了哈尼族习惯法对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影响。
这六个哈尼族村寨村规民约的制定者均为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制定时间最早的是倮厄村(1990年制定),最晚的为大鱼塘村(2009年5月17日制定实施)。这六个村寨的村规民约都涉及到生物资源的管理。
四、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上述六个村寨村规民约的分析并结合实地调查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哈尼族习惯法尤为重视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
对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的保护在所有的村规民约中都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表明哈尼族对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的高度重视。山顶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四度共构的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功能完善、已经达到动态平衡。但其作为一个人工生态系统,人为管理与自然调节同等重要,特别是山顶森林作为水源涵养地对维系整个哈尼梯田生态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山顶森林的完整保留,才形成了哈尼族地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独特气候。因此,哈尼族对于森林的保护极其严格,哈尼族不仅通过确定神山神林、定期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图腾崇拜禁忌等从观念意识的精神层面对森林进行保护,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村规民约对其进行保护。除大鱼塘村之外的其他五个村寨的村规民约中,明令禁止破坏森林、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惩处措施。
而在生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也有着详细的规定。如倮厄村村规民约对刺竹、竹子、竹笋、鱼腥草、老树、杉树、椽子等物种进行了特殊规定;坝美村村规民约对果木树、金竹、刺竹笋子等物种进行了特殊规定;全福庄村规民约对竹林保护进行了特殊规定;大鱼塘村村规民约对鱼、鸡、猪、狗、竹子、树、菜、玉米、豆等的偷盗行为进行了专门规定。另外,所有村寨的村规民约都对牲畜、家禽对庄稼的毁坏进行了专门的规定。这些规定不止以文本形式存在,更深深根植于哈尼人的观念意识中,时时刻刻规范着其行为活动,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哈尼族习惯法以经济处罚为主,且处罚力度很大
哈尼族村规民约中的惩罚方式几乎全部为罚款,即采取经济手段,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生活尚不富裕的哈尼人来说,经济惩罚足以对大多数哈尼人家形成足够的威慑,迫使其不敢违反规定。而哈尼族村规民约的处罚力度远远大于违规获益,如坝美村村规民约(2003年)规定:“擅自砍伐一棵树(不分大小),罚100元,砍一背柴,罚100元,砍一棵果木树罚150元”,“破坏龙树河周边大树,民族风俗活动地方,破坏一次罚1000元”,“向塘子里丢弃死牛烂马死猪死羊的,发现一次罚所丢进的同等价,丢进一只死老鼠罚50元。其他所丢进农药和鼠药的罚1000元”;倮厄村村规民约(1990年)规定:“在水源区砍1背湿柴罚15元,围地边乱砍发现一次罚5元,公路上下偷砍一棵行条罚200元,晚上加倍,偷砍老树,杉树罚300元,椽子每棵5元,偷砍叉叉每棵5元”,“乱砍刺竹每棵2角,竹子、竹笋每棵100元”;倮别新寨村规民约(1991年)规定:“牲畜吃毁庄稼应罚其主人40-70元”,“盗伐森林者罚款150-200元”;大鱼塘村村规民约(2009年)规定:“本村民头鱼、鸡、猪、狗、竹子、树、菜、玉米、豆等,抓着每个罚款200-4000元,又争吵者加罚200元”;全福庄村规民约(2007年)规定:“盗伐柴火者,砍着手指一样小的树苗时每背罚款20至30元,并责令要按照所砍株(珠)数的10倍补种赔偿损失,其余修枝、干柴、解放草等,视情节轻重每背罚款5-10元”;箐口村村规民约规定:“对违反本村村规民约的,视情节情况、认识态度,进行批评教育,情节轻微的进行警告,情节一般的50至200元人民币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元至1000元的人民币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将送司法机关处理”。
2008年,大鱼塘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74元,箐口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81元,全福庄四个自然村寨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89元、1017元、977元、1211元[[2]]。对这六个村寨村规民约中规定的处罚金额与农民经济收入进行比较,明显发现处罚力度很大,全福庄对盗伐者处以10倍赔偿,箐口村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最高经济处罚为1000元,几乎占一个村民年纯收入的六成,而大鱼塘村对本村村民违反村规民约的最高经济处罚为4 000元,是一个村民年纯收入的两倍以上。坝美村村规民约规定的最高处罚金额为1000元,超过红河县2003年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807元[[3]]。倮厄村村规民约规定1990年时的最高处罚金额达到300元,倮别新寨村规民约规定1991年时的最高处罚金额达到200元,以墨江县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3元为参照[[4]],倮厄村和倮别新寨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90年、1991年应该在200元左右,由此可见该两村村规民约规定的最高处罚金额高于其人均纯收入。
因违反村规民约而带来的高额罚金对于以农耕、畜牧为主且收入偏低的哈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哈尼族习惯法在哈尼人思想意识中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并渗入哈尼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维系哈尼族社区的和谐稳定、规范哈尼人的日常行为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三)哈尼族习惯法的执行和保障
哈尼族习惯法的执行依靠道德的约束、舆论的压力,其借助的是哈尼人对宗族、村寨的归属感。如上六个村寨的村规民约中都是只规定了处罚金额,而没有对采取何种方式执行进行规定。这是因为在哈尼人的理念中已经形成一个定规,即如果自己被认定违反了村规民约,便会无条件的接受处罚。一旦有人被认定违反了村规民约,但其拒不接受处罚,那么其接下来将遭受更为严重的处罚。这种处罚并非强制性的财产或人身权利的剥夺,而是社交活动参与权的剥夺,并且遭受村寨和宗族其他成员的指责、唾弃、漠视以及不作为。
在哈尼族社区,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力量相对于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压力是微不足道的,哈尼族社区内部的任何一个成员想要生存下去都需要借助社区集体力量的帮助。比如,建筑房屋对哈尼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务,如果单独依靠个人或单个家庭是无法完成的,在哈尼族村寨,当一户人家要建造房屋时,几乎全村每个家庭都会帮忙。笔者在元阳县箐口村调查期间,有好几户人家在修建房屋,但由于是民俗村,诸如砖瓦沙石等建材只能运到村寨边缘的停车场,需要人力将所有的建材背到家里,如果单靠一个家庭单是运输这些建筑材料都将占用数天时间,而当有全体村民的帮助时,只需一个清晨便可以解决。
另外,优良的稻种对于保证梯田产量至关重要,品种老化、退化以及同一地块他感作用的存在使得哈尼族社区一直存在着交换稻种的传统,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种植一个稻种3-5年便会同亲戚、朋友、邻居等交换稻种,尽管有时交换的是同一品种。若单个家庭脱离了社区,单靠自己的梯田进行稻种的选种育种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难度极大。
再者,个人和单个家庭在宗族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等哈尼族头等重要的事务中更是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如果一个人因为违反村规民约而被宗族和村寨摒弃,那么他及其家庭将不得参与宗族和村寨的任何集体性祭祀和宗教活动,当其家庭发生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时也将很少有人参与,而最为严重的则是被开除宗籍、村籍,不准入葬祖坟,这样一来,此人及其家庭将失去参与村寨一切集体活动的权利,其宗族和村寨归属感、认同感将完全丧失,不仅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面临诸多不便,而且在精神层面遭受沉重的打击。
坝美村村规民约第二十八条规定:抗交罚没款的,(一)财务抵押;(二)强迫干义务劳动;(三)点名张榜;(四)开除村籍。由此可见,关于声誉的“点名张榜”和近乎极刑的“开除村籍”对于哈尼社区成员的威慑是相当强大的。正是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哈尼人的人生理念保障了村规民约实际的法律效力和实质的强制性。
(四)哈尼族习惯法的演进及其同现行法律体系的差异和互补
当前,哈尼族习惯法正经历一个由口述性、零散性向文本化、制度化演变的过程。历史上,哈尼族村规民约大多是由村寨头人、摩批、咪谷以及有威望的人等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以口头形式在公众场合向大家公布,比如,咪谷或者摩批可能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或者节庆活动等公共场合下当中宣布一些规定作为村寨的村规民约。哈尼族传统的村规民约都是采用口头方式制定和传习的,这与哈尼族没有文字有着紧密的联系。哈尼族有着丰富的口述文学,这种文化传统为哈尼族习惯法采用口述形式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而现在,大多数的哈尼村寨开始将村规民约文本化,即以书面形式将村规民约记录下来并公之于众。
历史上,哈尼族的村规民约内容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是零散性,且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哈尼族传统上的村规民约类似于一部民法典,规范着哈尼人的日常社会行为,但是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内部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如今,哈尼族习惯法正在向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如坝美村村规民约分为:保护属于坝美管辖范围内的集体财产、保护个人财产、附则三章,共30条;倮厄村规民约分为:破坏树木、土地的相关处罚条例、牛马牲口糟蹋庄稼处罚条例、社会治安惩罚条例三部分,共16条;箐口村村规民约共有31条;而全福庄的村规民约则更具有针对性,专门针对村有森林资源管理。这表明,哈尼族村规民约正在逐渐朝着制度化、正规化、专门化方向发展。
哈尼族习惯法与现行法律体系最大的差异除了在表述方式方面一为口述化、零散化,一为文本化、制度化之外,是在执行方式方面的差异,现行法律体系依靠的是国家暴力,而哈尼族习惯法依靠的则是社区舆论,可以说一个是硬的制度的体现,一个是软的文化的表达。现行法律体系仅仅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表征,而法律规定以外的很多事情虽然在情理之中,但却很难用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界定。哈尼族习惯法则是更高层次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约束,相对于现行法律体系而言,哈尼族习惯法调解的范围更宽泛、更深入,对维持哈尼社区的和谐、促进哈尼社区的发展意义更为深远。
另一方面,现行法律体系与习惯法在哈尼族社区的普及度、接受度、实效性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以当地森林资源的保护为例,虽然全国人大早已在1984年颁布实施了《森林法》,云南省也于2002年颁布实施了《云南省森林条例》,但由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此类法规条例在哈尼族社区普及率很低,很多哈尼族村民对此知之甚少,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另外,由于我国法律体制尚不完善,法律执行力度较差,现行法律体系在哈尼族社区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实效性偏低。而哈尼族习惯法,即村规民约,因为是由村民大会或者村寨头人、摩批等制定,辖域很小,十分容易贯彻到每位村民的观念意识当中,普及性很高。同时,宗教意识、社会舆论对违规者产生的强大的无形的压力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惩罚,因此哈尼族习惯法的实效性很强,在哈尼族社区,鲜有违反村规民约而拒绝接受惩罚的案例。
现行法律体系仅对严重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有效,而哈尼族习惯法则在更为广泛的层面承担了调节社会内部矛盾、维系社会和谐的功能。村规民约对许多法律尚没有或者很难做出规定的方面给出了评判标准。因此,在哈尼族社区,习惯法或村规民约是对现行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当前哈尼族地区正在进行的由政府指导的村规民约的重新修订便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这说明,在国家法制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习惯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哈尼族习惯法与遗产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六个哈尼村寨的村规民约中可以发现,其对偷盗行为的处罚力度甚是严厉。例如,全福庄村规民约中规定“盗伐柴火者,砍着手指一样小的树苗时每背罚款20-30元,并责令要按照所砍株数的10倍补种赔偿损失”。坝美村村规民约规定“有偷盗行为的,一旦发现,按其偷盗物的30倍罚款,态度不好的重罚”,倮厄村村规民约规定“公路上下偷砍一棵行条罚200元,晚上加倍,偷砍老树,杉树罚300元,椽子每棵5元,偷砍叉叉每颗5元。… …”,倮别新寨村规民约规定“偷拿盗窃者罚款150-300元”,而大鱼塘村村规民约对于偷盗行为的处罚尤为严厉,其规定“本村民,偷牛者,找着每个人罚款10 000元至15 000元,又争吵者加罚5000元。… …”。由此可见,哈尼人对偷盗行为深恶痛绝,并竭力制止。
由于科学知识的欠缺、认识角度的不同,哈尼人对日益猖獗的“生物剽窃”事件并不知情,且毫无戒备之意。笔者在调查期间了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曾有一法国学者到元阳县搜集哈尼族传统稻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搜集到近百种稻种。哈尼人热情好客、慷慨大方的性格使得外来人员获得珍贵的哈尼族传统稻种轻而易举。因为哈尼族一直以来就有交换稻种的习惯,而这也是哈尼族培育稻种的重要方式之一。尽管哈尼族十分重视优良稻种的选育,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把优良稻种看做私有之物,而是乐于同他人或其他社区共享。正是这种交换稻种的传统,哈尼族才能够培育出数百种适应不同气候、土壤条件地区的优良稻种。
正因为哈尼人对优良稻种所蕴含的遗传资源的价值没有充分的了解,以及对“生物剽窃”事件毫不知情,使得哈尼族传统稻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生物剽窃”事件从本质上讲也属于一种偷盗行为,但是其形式较为隐蔽,而且是近些年随着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哈尼人对此十分陌生,并没有“生物剽窃”的概念。如果哈尼人真正认识到传统稻种含有的丰富、有价值的遗传资源,以及“生物剽窃”对自身利益的损害,依据哈尼人对待一般偷盗行为的惩罚态度,那么其将严格对待“生物剽窃”事件,并且会制定严格的管理措施。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机制对于抑制“生物剽窃”事件的猖獗发生将起到重要作用。
(六)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对哈尼族习惯法带来的挑战
随着哈尼族地区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哈尼族正处于一个文化大变迁的社会变革期。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转变上,如历史上以农耕为主的哈尼人越来越多的走上了出外务工、种植养殖、商贸等多种经营的道路,这进一步促进了哈尼族地区同外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的哈尼人的观念意识必定随之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哈尼人接受了现代思想,而传统观念则逐渐淡化。例如,哈尼人在历史上一直将土地视为珍宝,但现在由于农业产出值的相对较低,人们对于哈尼梯田的管理投入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降低,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了梯田荒芜的个别现象。
笔者在调研期间,了解到如下案例。元阳县箐口村2002年进行林权改革,将一部分林地划为村有集体林,但是当村委会与镇政府签订协议时发现,该村的集体林已经由本村村民李永禄(化名)承包,并且与镇政府签署了协议,承包期限为50年。而此事箐口村村民及委员会均毫不知情。箐口村集体林属于退耕还林地,所以政府每年都会给与客观数额的补贴,但是因为该林地已经承包于李永禄,所以收益都归李永禄所有,而理应是集体林产权持有者的箐口村村民却得不到任何收益。于是,村委会及村民大会都要求李永禄将集体林的产权归还全村所有,但是李永禄作为既得利益者,而且持有正规的与镇政府签订的承包合同,其坚称自己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拒绝将集体林产权归还全村所有。箐口村村民大会决定对李永禄进行惩罚,迫使其交还集体林产权,最后做出的处罚是禁止村民与李永禄一家发生社会交往活动,不许参加李永禄家的婚丧嫁娶等事物,这相当于哈尼族习惯法中的“开除村籍”,是最严厉的处罚。但是李永禄却不以为然,并且叫嚣钱财很多,离开了其他村民照样过得很好。事实证明,当做出处罚决定后,一部分村民仍与李永禄家保持联系,因为他们不想就此扯破脸皮,影响邻里关系。李永禄是箐口村最富裕的一家,其通过搞工程承包赚了很多钱,据一位村民称,李家财产至少在50万元以上,这对于一个普通哈尼家庭来说已是天文数字。箐口村村民大会见使用传统的惩罚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到镇政府协商解决,没有成功,于是便拿起了法律武器,将李永禄告上了元阳县人民法院,但由于李永禄托了人(据村民称),依然失败了,最后,箐口村村民大会将李永禄告上了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历了种种波折,直到2009年5月份才最终胜诉,将集体林的拥有权收归集体所有。
李永禄之所以敢违反村规民约,是因为其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充足的生存资本,而不必再完全依赖村寨或家族的力量,因此可以与社会道德舆论相对抗,而这对于处在小农经济时期的哈尼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案例表明哈尼族习惯法的权威性、实效性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情况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法院的裁决才最终维护了村民整体的利益,说明现行法律体系在哈尼族习惯法无法调解尖锐的矛盾时起着决定性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哈尼族习惯法在哈尼族社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带来的严峻挑战。哈尼族习惯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演进,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表明其是动态的,而且具有自我调适功能。哈尼族习惯法为解决国际广泛关注的生物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难题提供了一条潜在的途径,即自身管理机制的确定与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同时,哈尼族习惯法与现行法律体系在形式、内容、效用等方面存在着极强的互补性。当前,哈尼族社区正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对哈尼族习惯法进行修订,表明哈尼族习惯法在地区管理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哈尼族习惯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挖掘其精华,付诸于实践,对于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促进哈尼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加强哈尼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注[1]:箐口村、大鱼塘村、全福庄三个村寨的村规民约为田野调查时搜集所得,坝美村、倮厄村、倮别新寨三个村寨的村规民约摘自《红河哈尼族文化调查》。另:附录为箐口村、大鱼塘村、全福庄三个村寨村规民约的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