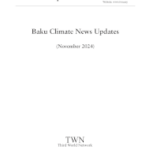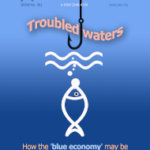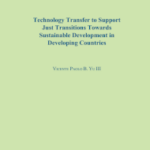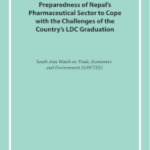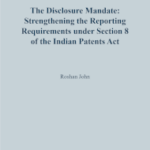传统生态知识:第三条道路(评述)
RAYMOND PIEROTTI1,2, AND DANIEL WILDCAT2
1Divis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Kansas, Lawrence, Kansas 66045–2106 USA
2Department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Haskell Indian Nations University, Lawrence, Kansas 66046 USA
翻译: 慕震
摘要:当代西方世界对于自然资源管理以及对待非人类动物和自然界的态度来源于西欧哲学传统,即,他们假定人类独立于自然界,并掌控着自然界。而另一种认识则来源于北美土著人民的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虽然TEK具有灵性导向,但其却融汇于西方科学道路上。TEK建立在对自然及自然现象的近距离观察基础上,同时它也结合了有别于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社区成员理念。TEK与特定的地理所在紧密相关,因此,包括动物、植物和地貌等物理空间的各个方面都可被认为是社区的一部分。所以,相对于西方政治和历史思维的时间导向,土著的世界观可以被认为是空间导向的。TEK还强调动植物个体以其自身方式存在。
这种空间感和对个体的关注让我们得出了TEK的两个基本概念:(1)所有的事物都有连通性,这与西方群落生态学在概念上是有关的,(2)所有事物都有关联性 ,这将理论关注的本质核心从人类转向为生态群落。连通性和关联性被纳入到很多土著民族的宗族系统中。在此宗族系统中,非人的生物被视作是我们的亲属,人类有义务对其予以尊重和崇敬。TEK与西方科学的融汇表明,在某些领域,TEK可能为西方科学提供洞见,或者甚至是新概念。因其关联着人类与非人类的一切,TEK本质就是多学科性的,TEK不仅仅是土著人民自然观念的基础,更是土著人民政治和道德观念的基础。这种多学科视角表明了TEK可能有助于解决各利益相关者和利益集团之间涉及自然资源利用、动物权益和保护方面的冲突。TEK同样可能规范人类对于其它生物的行为和义务,这是西方科学经常忽视的,起码是不重视的。我们从群落生态学和行为生态学中呈现一些案例,在这些学科领域,基于TEK的观察途径对自然现象得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非直观的洞见。诠释TEK可能有助于科学家们回应公众对于科学的感知变化,和我们社会中新的文化压力。
关键词:信仰体系;保护;生态学;环境;印第安人;土著;美国原住民;资源管理;传统生态知识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好比欧元硬币的正反两面。世界需要的不是关乎二者之间的选择,也不是关乎欧洲中心主义或欧洲至上主义与其对立面之间的选择。我们需要的是对欧洲传统整体的真正替代方案。
—Russel Means, Lakota
(quoted in Churchill,1995)
引言
在过去的100年间,在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人们中,关于对待自然界的恰当方式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争论((Leopold 1948, Dunlap 1988, Wilson 1992, Smith 1996)。有人主张发展优先(Pro-development)的攫取方法,自然资源主要按照其带给人类的经济价值这方面来被认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对环境问题和资源管理的态度都占据着主导地位(Dunlap 1988),并被目前的“明智使用”(wise-use)运动所体现(Lehr 1992)。这一观点已被视为政治正确(Smith 1996);然而,开发利用的做法可能来自各种政治立场。
当然,也存在着反对立场,他们认为自然和非人生物必须免受人为干扰,并且真正的保护手段应该是从人类居住区拨出大片土地给它们,甚至包括人类自己也应被排除在外(Brinkerhoff Jackson 1994, Owens 1998)。例如,1964年的美国《荒野法案》(U.S. Wilderness Act)定义荒野为永远不受人为干扰的空间(Owens 1998)。这一观点虽然被认为带有左翼政治色彩,但对于发展优先的力量而言,其在政治立场上代表了“保护主义者”(Wilson 1992, Smith 1996)。
尽管存在明显的差异,所有关乎自然的西方观点都来自相同的欧洲哲学根基,即,笛卡尔,培根和启蒙运动(Smith 1996)。不同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的著作中,它们都假设人类自主于自然界,并掌控着自然界(Mayr 1997)。例如,John Locke(1952)认为,自然之所以存在主要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舒适与方便。在这里,我们假定我们所描述的观点是现代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社会中的主导文化特征,这些社会里有大比例的公民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自然因此被视为隔离起来,并“被控制”了(Smith 1996)。在这些社会中,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将自然界看成是“资源”的组成部分,因此暗示着他们认为自然界所有东西不论是出于经济目的还是美学目的,都可被利用(如,Locke 1952)。此外,工业化社会中的公民通常认为自然界的定义应该是与人类分开的地方(Leopold 1948, Smith 1996, Owens 1998)。因此,问题不在于缺乏对于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知识,而是在于如何鼓励人们去保护(Anderson 1996)。
然而,我们这里并非要对西方的自然观有所审视与分析,因为这个话题已是老生常谈(Smith 1984, 1996, Mander 1991, Deloria 1992, 1995, Jackson 1994)。我们的本意是探讨美洲土著人民的传统生态知识(以下简称为TEK),我们相信这代表了第三条道路,既融合了开发和保护这两方面共同的因素,还保留有两者的明显不同(Johannes 1989, Martinez 1994)。我们之所以强调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知识是依据我们个人的经验和知识评判的,但需承认的是全世界土著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的形式都有着类似的主题和方法。
一些保护主义人士分辨说,他们使用的方法来自美国土著民的精神或土著传统(Pierotti 和 Wildcat 1997a, b)。我们认为,这样的联想是基于对土著信仰系统真实本性的错误假设之上的。因为不同与西方哲学,TEK的假设是人类是且永远是与自然界相联系的,而不存在独立于人类和他们活动的自然界(Deloria 1990, Pierotti 和 Wildcat 1997b,Owens 1998)。
TEK在连通性(connections)上有其残忍的一面,就是攫取(extraction)——例如,动物作为猎物被捕获——就与非人生物的内在价值和利益的认知互相混合在一起(在Taylor 1992文献意义上如此)。传统知识的基础前提是,人类不应该将自己视作理应对自然负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自然界的管家,而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不比别的部分更胜一筹(Pierotti and Wildcat 1997b)。如此,TEK更多的是致力于激发人类对其它生灵的敬畏,TEK这种对生灵的内在敬畏可以约束人们滥用自然界的倾向,因为非人生物也被包含在群落的正式代表中,并被视作是群落的成员(Anderson 1996, Barsh 1997, Salmon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