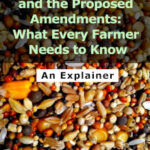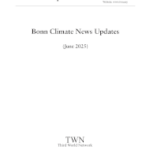理智对待“生物剽窃”
来源: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
作者:David Dickson
如果不想让生物多样性本身遭受损失,反对生物剽窃的斗争必须既考虑到正规的科学研究又考虑到社会正义。
长期以来,科学家或明或暗地参与了发达国家寻找和确保自然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工业化或者维持他们自己生活标准。
这是19世纪许多探寻和测绘非洲中部的“科学”考察背后的动机。最近,研究地方药物又成为了一种从植物中发现可能具有现代药物价值活性成分的划算的方式。
随着商业和经济动机在这样的“科学”事业背后涌现,人们不可避免地对于这种单向的利益流向越来越感到气愤。为此,国际社会制订了措词强硬的协议,用于促进社会正义。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协议就是1993年生效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赋予了各国对其境内的动植物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贯彻这类协议的努力常常导致科学家的抗议。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以前收集、转移和分发研究样本的自由,他们把事先审批的要求视为繁文缛节,认为它们常常会导致项目的延迟。
抗议之潮
最近,一位荷兰出生的科学家Marc van Roosmalen被巴西投入监狱。van Roosmalen在巴西的雨林里工作超过了20年时间,他的工作让好几个新发现的灵长目动物得以命名。他被关押成为了科学家愤怒的焦点(见 科学家威胁举行罢工抗议灵长类动物学家入狱)。
Van Roosmalen此前为国立亚马逊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的所在地Manaus位于亚马逊地区的中心。但是如今他自己开设了一个私人研究所。今年6月,他被判刑将近16年,理由是违反了为保护巴西无主自然资源而制定的法律。
他的遭遇引发了科学家的抗议之潮——最初是巴西科学家,最终扩展到了国际科学界。对于许多科学家而言,该案象征着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然环境让科学界不公平地受害。
例如,热带生物学和物种保护科学家协会正式地把van Roosmalen的遭遇描述为一个政府支持的“对生物学家的实践和职业的攻击”,并呼吁立即释放他。巴西的最高法院上个月确实暂时释放了van Roosmalen。
是非曲直
然而,van Roosmalen的案件可能比它最初登场的时候更加复杂。首先,他被指控“不适当占有”——这与他决定用资助者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物种有关。尽管过去这种做法被广为采用,如今它引起了科学界自身的疑虑。
而且,很明显,按照巴西法律,van Roosmalen捕获和饲养他研究的一些动物需要寻求许可。他对冗长的申请程序感到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获得许可,他的实验就是非法的。
但是人们普遍相信其他一些同样感到失望的科学家未经许可就收集样本却没有面临法律诉讼。事实上,van Roosmalen的一些支持者把他受审归结于他与有政治影响力的土地拥有者在拯救亚马逊雨林的运动中的公开冲突,而不是因为当局热衷于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无论是否存在不正当的政治压力,很明显巴西和其它国家的当局没有配备有效开展工作所必须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批准试验的过程被长期耽搁,这让各方都感到失望。
说服工作
科学家可以据理力争说,这种耽搁对于他们的研究代价昂贵,而且他们本身可以对制定贯彻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政策、法律和规定做出有用的贡献。
但是当他们用自由的名义为他们自身的科研利益辩护的时候,他们的理由就被他们前辈的罪行削弱了,有时候他们的同行也犯下了这类罪行,这些人对这种自由的滥用加剧了当前的严重局面(见 发展中国家“需要遗传资源法规”)。
物种保护者在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衍生管理规定辩护的时候也有一个理由,即它们是保护当地动物群和植物群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武器。但是,谁正当地“拥有”这些材料的诉求常常比保护人士所承认的更为复杂。保护人士还需要承认一个健康的科学基础对于他们的事业至关重要。(见 所有权之争妨碍物种保护)。
避免双输局面
幸运的是,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局面已经显著改观了。当时在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后,发达国家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几乎冻结了。谨慎的谈判已经产生了有效的指导方针(例如关于分享样本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表明了调和是有可能的。
但是正如van Roosmalen案件引起的强烈情绪所表明的,仍然存在很大的张力和不信任。因此科学家和物种保护者,特别是后者中的积极分子,都必须记住他们对于合理设计和有效实施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机制拥有长期的共同利益。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当管理规定被忽略或者被过于热心地执行的时候,没有人是赢家。